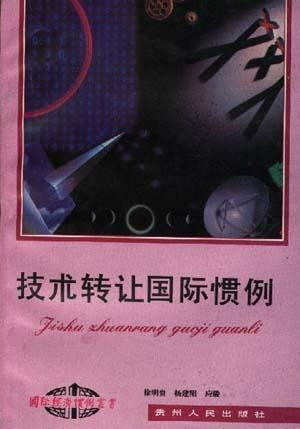二叔是村里有名的木匠,去年廠里新上了數控雕刻機,他一直念叨想學。這周末,他提著兩袋自家種的花生進了廠,有些局促地說:“大侄子,我就看看,不耽誤你們干活。”
我把他領到機器旁,演示了一遍基本操作,講了不到二十分鐘,車間主任就喊我去處理急單。走時我叮囑二叔:“累了就去休息室喝茶,食堂十二點開飯。”
訂單棘手,一忙就到了十二點半。食堂師傅打電話問:“你二叔怎么還沒來?給他留的排骨快涼了。”我心里一緊——車間設備昂貴,操作不當后果嚴重。放下電話就往車間跑。
推開門,午后的陽光斜照進車間。二叔背對著門,站在已關機的雕刻機前。他左手捏著個小木塊,右手握著我的舊鉛筆,正對著操作面板的按鈕,一筆一畫地在木頭上臨摹那些英文標識。他腳邊散落著七八個木塊,有的畫著流程圖,有的標著操作步驟,字跡歪斜卻極認真。
最讓我鼻酸的是,每個按鈕旁都用小字標注著他自創的“土味翻譯”:START旁邊寫著“開”,EMERGENCY STOP旁邊是“救命停”,FEED RATE邊上注著“走快走慢”。他聽見動靜回頭,慌忙把木塊往身后藏,像個做錯事的孩子:“我看你們都忙,就自己琢磨……沒碰機器,真的。”
他攤開手心,那些被鉛筆灰染黑的手指微微顫抖:“年紀大了,記性不好,想著畫下來帶回去晚上看。”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,真正的“技術轉讓”從來不是單向的給予。這個只讀過三年小學的老人,用最笨拙的方式向我展示了何為“敬畏”:敬畏知識,敬畏機器,更敬畏不給人添麻煩的尊嚴。他臨摹的不是按鈕,是一個農民對工業文明的朝圣。
我扶著他去食堂,排骨果然涼了。但二叔吃得很香,他悄悄對我說:“下周末我還來,把‘自動換刀’那塊搞明白就行。”陽光照在他花白的頭發上,那些鉛筆字跡在他指縫里閃著光——那是比任何技術參數都動人的轉讓協議,簽字的筆是汗水與時間,見證人叫傳承。